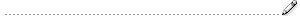“那是我小时候,常坐在父亲肩头,父亲是儿登天的梯,父亲是那拉车的牛……”每每听到这首歌,眼前总浮现父亲那瘦削却挺直的肩膀。
父亲的肩膀,就是我童年的天堂。
听母亲说,我出生后,父亲就像中了彩似的,整天乐呵呵的。我半岁前,经常被父亲揣在棉衣里。半岁后,就经常骑在父亲的肩膀上。父亲顶着我遛弯,我就把他的肩膀当马,把他的头发当缰绳,张开脚丫子撒欢,揪着他的头发笑哈哈。重男轻女的爷爷总是埋怨父亲:“丫头片子,别把她宠上天了!”父亲总是笑着说:“这是我的女宝呢!”
那年,村里开始养蚕,为了能让蚕宝宝吐丝结茧,大人们便会用麦梗做一条条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“毛毛龙”,然后将快要吐丝的蚕宝宝放在毛毛龙上。调皮的我不小心被麦梗刺伤了眼睛,几天下来眼屎像胶水一样沾满了双眼。我越看不见越哭,越哭眼屎就越多。黑暗中,我尝到了失眠的恐怖。
父亲背着我去镇上看眼睛,那时候没有公交车,父亲背着我走了五公里路,一路走还一路给我讲故事,讲武松打老虎,讲诸葛亮的空城计。搂着父亲宽厚的肩膀,我内心注满勇气和力量。
父亲的肩膀,是全家人坚实的依靠。
那时候爷爷常年在外,奶奶体弱多病,家里缺少劳动力。父亲是老大,家里苦点累点的活都压在父亲的肩头。奶奶告诉我,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,挑水担柴,健步如飞。
闹饥荒那年,听说望亭有南瓜卖,只有17岁的父亲,硬是将从那里挑回了150斤的南瓜。从望亭到官桥,有六十多里的路程呢!父亲回到家时,天已擦黑。他的饥肠辘辘的四个姐妹见到南瓜就剁了去煮。只有奶奶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撩起父亲破旧的衣衫,在他血肉模糊的肩膀上,轻轻地涂上一点红药水。
父亲的肩膀,是我永远的精神故园。
父亲现在已是古稀高龄,原来挺拔的脊背已经微驼,仍不顾儿女的反对,接受一家绿化公司的应聘,不管刮风下雨,继续奋战在绿化的第一线。
当人们趟洋在苏州博园,欣赏那美丽的花卉盆景时,也许不会注意到有一个老人,正用微驼的肩膀扛着一台除草机。那就是我的父亲,一个永远也不肯闲下来的老人。他弯而不屈的肩膀,是我永远的精神故园。